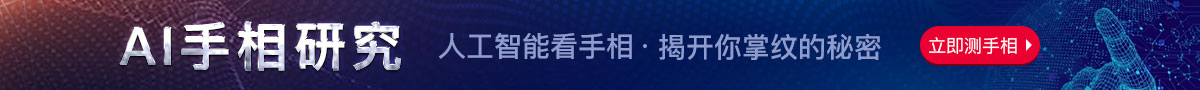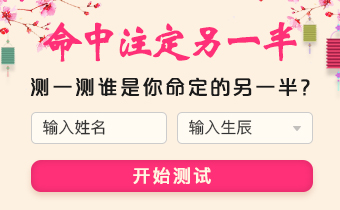求姻缘解签铁树生花久生男八十三疏林筛月影满(八十三签解签 姻缘)
2023-06-18 10:24:05 | 1090人围观 | 金牛座运势麦收八十三场雨,不是80多场雨,是在农历八月十月和来年三月,只要各下一场透墒场,冬小麦便可获得丰收。眼见的丰收正一点一点被毁去,小麦不贪,农民也不贪,何来如此的惩罚!

经得起百日旱,经不起十天涝,再一次读懂了这句谚语。我在旱塬上长大,从小就知道农民抗旱的艰辛和劳苦。为了栽活一棵庄稼苗,他们曾日夜不息地刮破了井底——黄汤水也是水啊,拉一辆架子车,到数里外往回拉水更是那时候的日常。“锄头有水”,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三十八军战士口含一块石头,克服饥饿坚守阵地,该是一样的道理。

记忆中,这情景曾有过一次。有二十年了吧,人们种上麦子,没等来十月的透墒雨,没等来冬天的雪被子,“一冬无雪天藏银,三月有雨地生金”是那一年春节最容易让人记住的春联。结果从三月到四月,人们也没有等来一场透墒雨,麦穗瘦小的像蝇头线垴。五月底,要收麦子了,却是一连串的阴雨天。我阴差阳错从乡亲那里又认识了一句谚语:麦返青憋满仓,谷返青一把糠,也切肤一般知道了:成熟的麦粒就麦穗上生芽、成长、抽穗,是多么恐怖的一回事。几天之后,许多地块收的麦子抵不住收割机的费用——青麦秸筒比麦籽和麦糠还多。
几个的老乡,挤在村头的一家门楼下。我停住车,和他们一起埋怨着,惋惜着,无奈着,愿意着,希望着……
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,说不定明天就是晴天呢。“xxx你没事,一到时候工资按月都来啦”,亲切里我读出了“杨二嫂”的尖利。我也盼着来个大丰收啊!
再驾车前行,我想起《观刈麦》里的诗句:”今我何功德,不曾事农桑;吏禄三百石,岁晏有余粮;念此私自愧,尽日不能忘。”一千多年前,诗人杜甫如此,现在也一样。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,心怀农民始终是社会最朴素的良心。

十多天前,还和母亲商量:要么把陈麦粜了,要么再买个粮仓。今天我一进门,母亲就是一番怨天尤人的怼落:啥时候种地才能不再靠天吃饭。家有藏粮,心中不慌。你还说粜了?
手机里又有了新段子:谁认识女娲?出来说说,赶紧给天补补。神话故事里有女娲也有后羿,说明远古时代人类生存环境更恶劣——旱和涝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,但人们都能战而胜之。在中国的神话故事里,英雄们没有翅膀,也都是以普通人的形象出现的。
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骨子里的自信。

相关内容推荐:
- 热门阅读
- 推荐阅读
- 最热文章
- 专题列表
全站搜索